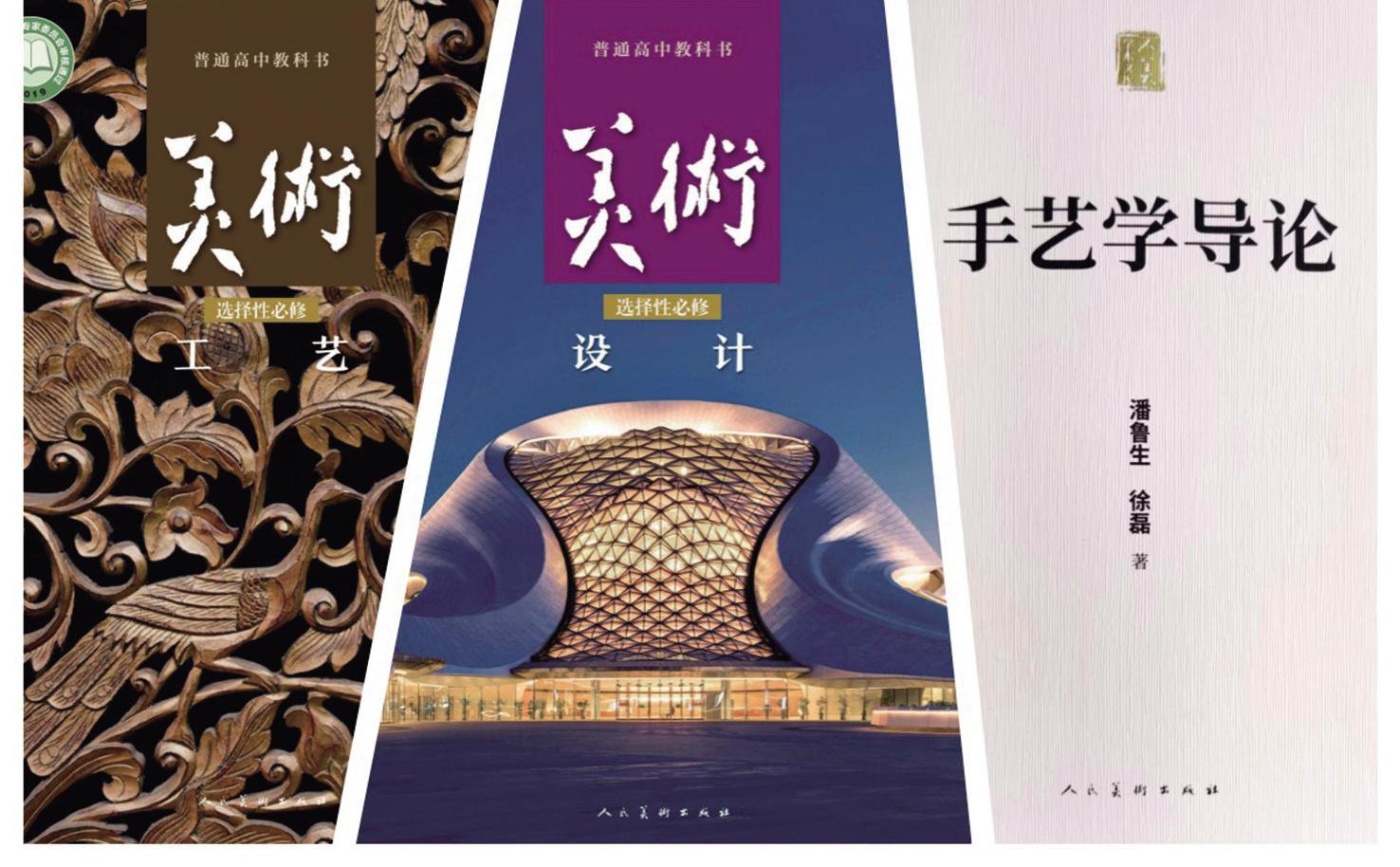2017年12月9日下午5時許,“東亞杯”中韓足球隊對決賽2:2落幕時,武漢大學(xué)同學(xué)群一條信息突然映入眼簾:譚老師千古!
“譚老師走了,錐心之痛,夜不能寐。欲為武大學(xué)子哭先生!”當(dāng)晚,我強(qiáng)忍悲痛搜索思緒,譚先生音容笑貌便一幕一幕地浮現(xiàn)在我的眼前。
一、入門
1993年,我在中國人民大學(xué)就讀“福特班”時已知譚先生,他是中美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交流委員會(福特班)的中方委員。1995年和1996年,我又在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研討會上兩次見到譚先生。譚先生給我的印象是:身材高大挺拔,不怒自威,可能不太好接近或者說有點嚴(yán)厲。那會兒,我確實沒有勇氣與他接觸。
1997年,我有幸考上了武漢大學(xué)商學(xué)院博士研究生,成為譚門弟子郭熙保老師的第一位博士生。這下,譚先生成了我的師爺!那年10月,中華外國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說研究會學(xué)術(shù)年會在江西財經(jīng)大學(xué)舉行,就這樣我與原本以為“可怕”的師爺有了親密接觸。
“小張,你原來有沒有想過要報考我的博士?”一天,譚先生問我。
“譚老師,您名氣這么大,看上去又非常嚴(yán)肅,我根本不敢報考您的博士?!蔽覍嵲拰嵳f:“后來,我才發(fā)現(xiàn)您實際上和藹可親。”
會間,有位老師發(fā)現(xiàn)我與譚先生、郭老師在一起,就建議我們祖孫三代在一起合個影吧。 “希望很快有第四代出來!”另一老師說。
由于我才入門一個月,只能謝謝這位老師的鼓勵!但后來個人的成長之速出乎所料。
2008年,我?guī)У囊粋€博士生順利畢業(yè)了,譚先生門下真是有了第四代學(xué)生!譚先生獲知后露出了開心笑容。
如今,我又有一位博士弟子評上了博士生導(dǎo)師。譚先生若泉下有知,該會多高興??!
二、傳道
在我讀博士期間,譚先生不顧自己年近80高齡,堅持給我們講授“發(fā)展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”課程。那時,上課地點是當(dāng)時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二樓教室,譚先生每次都會大清早按時趕到。
有次上課情形讓我終身難忘。那天早上,譚先生一改平日溫和、平緩的語調(diào),用有點急促、氣憤的聲音對我們說:“今天早上7點多鐘,有一個學(xué)生打電話給我請假,說他現(xiàn)在黃石看望生病的外婆。這是請假嗎?8點鐘上課,7點多還在黃石?這分明就是不想來上課嗎!”稍頓,譚先生用緩和一點的語氣對我們說:“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:我執(zhí)教50年,從未遲到過1分鐘!”。當(dāng)時,教室里鴉雀無聲,我當(dāng)時的感覺只有一點:震撼!
之后,我每次上譚先生的課都提醒自己:千萬不要遲到!終于有一次,當(dāng)我走進(jìn)教室時,發(fā)現(xiàn)譚先生已經(jīng)端坐在那里了。我心里一緊:遲到了!于是趕緊貓著腰坐在了后排。譚先生看著我,笑了一下:“不用緊張,你沒有遲到,今天是我早到了一點?!蔽疫@才松了口氣。
三、畢業(yè)
2000年初夏,我迎來了博士論文答辯。當(dāng)時,江西財大正在全國范圍內(nèi)引進(jìn)博士,后來我所在的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黨總支江建強(qiáng)書記親自趕到武大參加我的論文答辯,據(jù)稱這是當(dāng)時江西財大黨委書記伍世安教授親自對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提出的要求。那天,我?guī)Ы瓡浀阶T先生家拜訪。在說明來意以后,譚先生非常熱情地說:“江書記,我們又見面了。來,請江書記上座!”
在博士論文答辯的中途休息時,譚先生帶著我到商學(xué)院黨委書記辦公室,指著我對當(dāng)時的學(xué)院賀書記說:“江西財大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的江書記到了我們這里,他是專門來參加小張的博士論文答辯的。賀書記,你看人家江西財大是多么重視人才??!”賀書記聽了,連連點頭說:“您說得非常對!譚老師,我們要向他們學(xué)習(xí)?!?br />
四、慈愛
畢業(yè)以后,我多次回到武大,都會去看望譚先生。每次,譚先生都熱情地接待,耐心地聽取我匯報成長經(jīng)歷,并對于我的困惑給予認(rèn)真的解答。
我曾經(jīng)幾次跟譚先生匯報自己從“仕”的經(jīng)歷:曾經(jīng)做過江西財大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院副院長、《當(dāng)代財經(jīng)》副主編、科研處副處長、處長以及外事處處長。譚先生多次語重心長地對我說:“進(jìn)銘,你不斷地取得進(jìn)步,我很高興!不過,你要記住一點,在做好行政的同時,一定不要放棄了學(xué)問!”“我在武大讀書的時候,朱光潛先生曾經(jīng)教我們一句話:“You should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, then you should 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”。
有時,當(dāng)我跟譚先生講起自己的種種“不如意”時,譚先生都會給我積極的開導(dǎo)和鼓勵。譚先生多次跟我講起抗戰(zhàn)期間在武大(樂山)求學(xué)時的艱苦條件和大家認(rèn)真求學(xué)的故事。他還曾經(jīng)跟我講過程千帆先生在武大的故事。我有幾次發(fā)現(xiàn),當(dāng)我從譚先生家里出來以后,自己怎么都打不開的心“鎖”,竟被師爺輕而易舉地“打”開了。
有年夏天,我去看望譚先生,自然聊到了避暑。我問譚先生有沒有到過廬山?譚先生告訴我,沒有!于是,我對譚先生說:“譚老師,我回去可以試著聯(lián)系一下;聯(lián)系好了以后,就請您和師母在廬山小住一段時間?!弊T先生對我說:“進(jìn)銘,謝謝你的好意!我和你師母年紀(jì)都大了,不能給你們添麻煩了。世界上沒有去過的地方很多,沒去就沒去吧?!?br />
2010年,我去看望譚先生。譚先生問我:“進(jìn)銘,我有沒有送你我主編的一本書?”我說:“好像沒有?!弊T先生有點吃力地站起來,從書房拿出一本厚厚的《發(fā)達(dá)國家發(fā)展初期與當(dāng)今發(fā)展中國家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比較研究》贈我。當(dāng)時,他在扉頁上寫下這樣的話:進(jìn)銘老弟存書 崇臺贈 2010。
那一刻,我感受到的是先生的幽默和師爺對徒孫的關(guān)愛!
先生不死,只是慢慢隱去!我想,在櫻花盛開、丹桂飄香、楓葉映紅、梅花綻放的珞珈山旁,發(fā)展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的大樹已然根深葉茂并將繼續(xù)成長。
先生若然有知,必當(dāng)含笑九泉!
(原文首發(fā)于2018年4月3日中國文明網(wǎng),本報編發(fā)時有刪改)